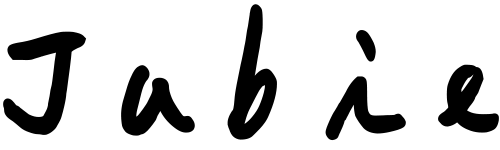照片不見了。
本來應該躺在櫃子裡的一疊照片不見了,我慌張地在房內來回翻找,無止盡對自己盤問:搬家前最後一次見到是在哪裡?妳確定嗎?妳再好好想一想。
那一疊照片是我小時候的家庭照片,前年辦婚禮特別挑選,從台東帶上台北。後來沒用到,就一直收在五斗櫃裡。前陣子搬家,置物系統大洗牌,新的定位還不熟,記憶像是失靈的羅盤,一直指向舊的地方。這次打算寫一些關於母親的文章,腸枯思竭時想到我有小時候的照片吶,拿出來看看或許有靈感。但現在不只靈感迷路,連珍貴的照片都失蹤。
我翻遍五斗櫃,卻滄海桑田,五斗櫃裡現在是一片保健食品。我頹坐在張口吐信的櫃子前,像個失落的歷史學家,連自己的歷史都找不到。找不到就算了,這件事情可不能讓母親知道。
母親是一個收納達人,同時也是斷捨離天后。她從來不囤積什麼當作紀念,唯有老照片,她視若珍寶,收納成冊。記得小時候我們要把相片抽出來看,她總是連聲阻止。這樣子看就好。你們小心手指不到摸到照片中間。那些她細細珍惜,按照時序整理排放的,是我和我弟弟的童年。有我們出生、喝奶、洗澡、出遊,那些再也無法回放的,就定格起來被她收藏。她說這些照片沒了就沒了,很珍貴,不可以亂拿。我結婚的時候,摸了幾張出來,有種做賊心虛之感。
老家的照片本厚重,也是放在這樣的櫃子裡。上漆的木頭,雕琢過的把手,得吃力地拉開。母親熱愛歐式古典風格,把家裡佈置得像英國莊園(甚至在冬天也能穿短袖的台東,裝了一台根本無法使用的壁爐)。後來我上台北搬家,四處添購傢俱的時候,眼光怎麼樣都離不開歐式鄉村風。買了一組木書桌椅跟五斗櫃,有著彎曲的桌腳,抽屜把手雕成了母親最愛的玫瑰,母親見到後連聲稱讚。
早知道就不要拿了。想到母親要是知道這些珍貴的照片(為了結婚我還挑了最經典的那幾張) 被我搞丟,不知道要怎麼數落我。放棄五斗櫃,我轉向書桌下的小抽屜,上窮碧落下黃泉,動手動腳找東西。
未果,卻一抬頭就撞上桌子。大片桌版硬朗,招呼我的腦門,痛裡竟有種熟悉的感覺。總是這樣撞到頭的。那時還小,母親是紙黏土老師,訂做了一張又長又大的木桌子,佔據大半的客廳,就當工作桌。母親在桌子上憑空捏造,用黏土捏出童話世界;我和弟弟就在桌子下無中生有,用玩具建起秘密基地。母子三人忙得不亦樂乎,我和弟弟玩到忘我時,也常常一抬頭就撞上桌子。
同樣都是大木桌,母親的桌總是潔淨整齊,而我的總是雜亂無章。藝術家的基因遺傳了,收納的基因倒是斷層。如果被知道照片不見了,大概又會被碎念,就是東西都亂丟不整理好,才會找不到。
我奔走在新家,翻箱倒櫃,打開一個盒子又一個,往深處往縫隙探照挖掘。找東西就像是考古,帶著疑惑,一層一層撥土。人總是這樣,把重要的東西放在重要的地方,然後把那個地方徹底遺忘。
絕望之下已經午夜,不甘願地梳洗更衣,文章也沒寫,照片也沒找到。在更衣間,想著心中一直想找的那張照片,是年輕的母親抱著幼小的我,母親迎著風長髮飄逸。人人都說母親年輕時時髦,穿著最流行的衣服,是個熱愛打扮的女子。
記憶中母親的衣櫃,有一件我最愛的水藍色澎澎袖長裙。矮小的我穿上,裙擺會拖著地板,轉圈圈的時候飄起,像個公主。我總是轉啊轉的,看著裙擺像藍色花瓣圍著我展開,在半空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樣子。最後暈頭轉向,抱著裙子倒在母親的床上。因為太愛這件裙子了,還曾經跟母親說以後我長大就送我吧。母親笑道,哎唷,妳長大就會有更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了啦。
後來我在台北街頭,偶然看見一件水藍色連身洋裝,有著澎澎袖和大裙襬,便二話不說買了下來,儘管少有場合能穿上。
小時候喜歡趁母親不在家,偷偷打開母親的化妝品,有樣學樣。母親的梳妝台很寬敞,有一個大圓鏡獨自聳立,臂展長的桌面成弧型,明亮大方,把人環在中央。相比母親的梳妝台,我現在的梳妝台顯得羞澀,方正的鏡子上方有層層系統櫃,嵌在更衣間的一個角落,被光線遺落,顯示主人不重視打扮。儘管如此,總還是有跡可循。因為懶得研究,母親慣用的品牌順理成了我慣用的品牌,在母親梳妝台前排排站的,現在也零星出現在我梳妝台前。不用再偷偷來,長大後很多事情都正大光明了。正大光明,變成和母親相似又相反的樣子。
我看著梳妝台上方的系統櫃,還有一兩個盒子,放著平日少用的瓶瓶罐罐。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,站上椅子把盒子拿下來,在各種雜物堆疊裡,沿著盒子四周仔細摸索。
找到了!是一疊舊照片,在盒子最邊緣。
終於找到了,是我心心念念的照片啊,終於不用被媽媽嘮叨了。歷史學家找回歷史,考古學家找到珍品,簡直舉國歡騰。偷拿照片的罪惡感瞬間被我拋之腦後,我跳下椅子趕緊拿去給老公看:「你看這是我小時候!」
照片裡是好久好久以前,一張張翻回去,熟悉的場景裡站著更年幼的我。藏那麼深的舊照片好像有它的巧思,循著新家沿路翻找的過程,回憶湧現像是指路,細數著媽媽如何影響著我的生命,就發現了軌跡。像照片一樣,珍貴且無法竄改的,就定格在血液裡。照片裡年輕的媽媽抱著幼小的我,媽媽迎著風長髮飄逸的樣子,很像我現在的樣子。